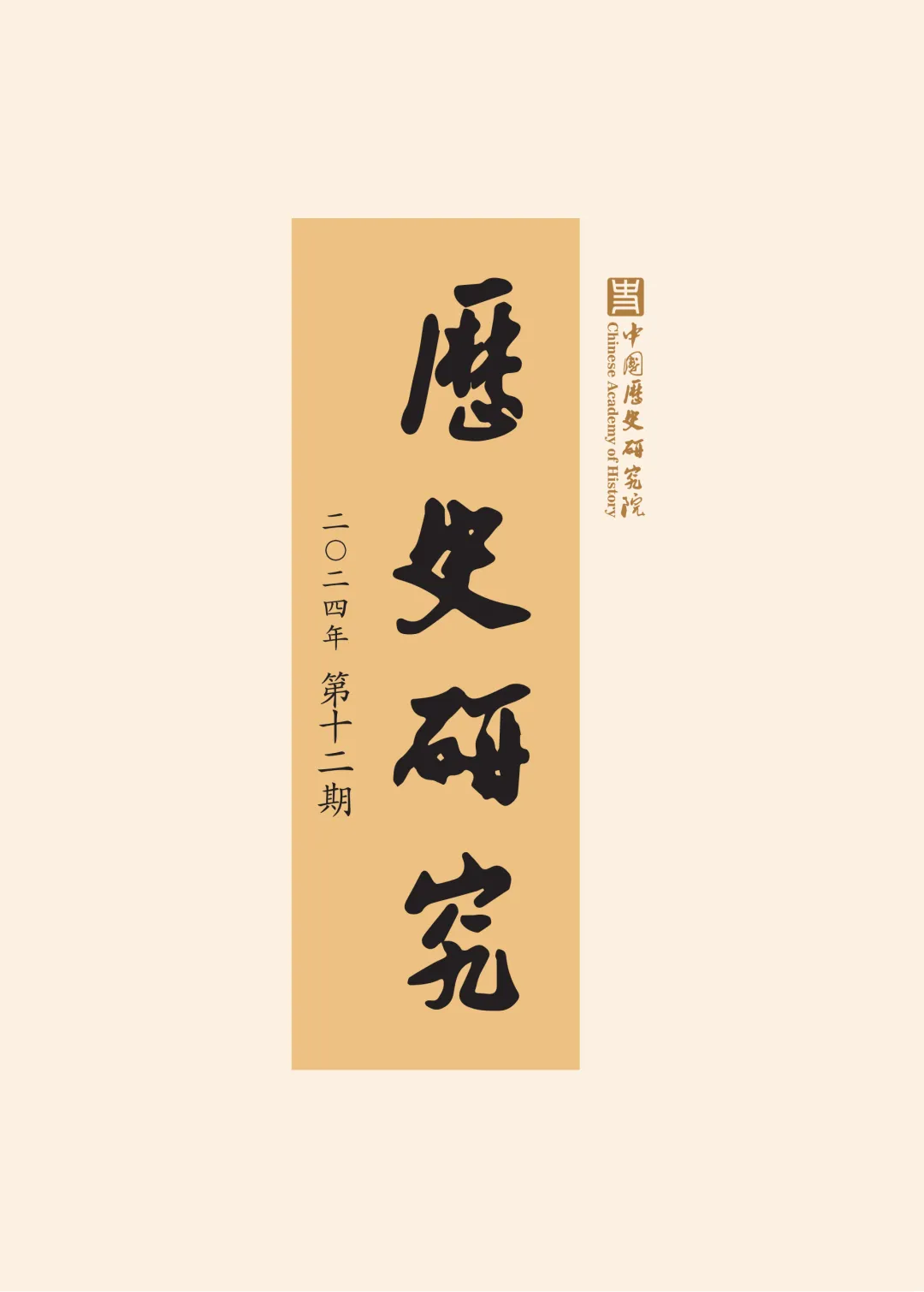
摘要:以跨学科视角回顾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古文献学等学科对古文字学形成和发展的推进,从古文字材料整理、各类工具书编纂、古文字考释和专题研究,以及学科建设等方面可以勾勒出我国古文字研究和学科建设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古文字研究和学科建设,要围绕加强理论综合研究、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以及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应用等关键环节,着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古文字学自主知识体系和新兴交叉学科。
关键词:古文字学 古汉字 交叉学科 自主知识体系 数字史学
古文字学是以古文字(即“古汉字”)和各种古文字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建立的一门新兴学科。[1]百余年来,随着我国现代人文学术兴起和不断进步,尤其是考古学发展和层出不穷的古文字新资料问世,在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古文献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参与和推动下,古文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逐步形成并持续发展。[2]2019年,甲骨文发现与研究120周年之际,学界开展了系列纪念活动;2020年,国家有关部委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古文字学这一冷门“绝学”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新时代背景下,回顾古文字学发展历史,分析当前我国古文字学研究现状、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展望未来,对进一步推进古文字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建构很有必要。
一、多学科浸润滋养的古文字学
晚清时期,古文字学从传统金石学中分立,百余年来,在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古文献学等多学科的共同浸润滋养下,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
现代史学研究与古文字学科发生关联,源于对古文字史料价值的发掘。对历史学研究而言,“史学便是史料学”,而史料有“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之别。古文字资料的新发现,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可信的“直接史料”,也可以用来校正“间接史料”。因此,傅斯年认为:“新史料之发现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3]历史学者以广阔的历史视野,运用现代史学理论和方法对古文字资料开展整理研究,为古文字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王国维运用“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互证的“二重证据法”,以甲骨文材料与《史记·殷本纪》等文献互证,不仅凸显甲骨文的重大史料价值,还“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4]王国维的研究方法对古史与古文字探究产生深远影响。郭沫若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论引入古文字研究领域,利用甲骨文、金文资料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在甲骨文资料分类整理和释读、两周金文断代和分国,以及有关古文字考释等方面成就卓著,开辟了古文字研究的历史新阶段。[5]20世纪30年代以来,依据古文字资料研究相关历史问题者名家辈出,胡厚宣在科学整理甲骨文资料、开展殷商史专题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就,[6]徐中舒、唐兰、于省吾、陈梦家、张政烺、李学勤等在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简帛文字材料和古代史研究方面发表一批有重要影响的论著。[7]除这些代表性史学名家外,文史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出土古文字与相关文献资料研究上古历史问题,成为20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
历史研究对古文字学科形成和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古文字资料作为“直接史料”的重视和利用,促进古文字资料的科学整理,为古文字学科发展奠定资料基础。二是通过对古文字资料历史价值的挖掘,凸显古文字学对上古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引起更多学者对古文字学的关注和研究。三是建立在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资料基础上的历史研究成果,揭示古文字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巨大价值,确立了古文字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重要地位。四是历史学者的历史视野、理论和方法促进对古文字资料历史文化内涵的发掘和阐释,为古文字释读提供更为可靠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助于更准确地分析古文字构形及其发展演变,提高古文字释读和阐释的科学水平。
现代考古学新发现的各类物质文化遗存,开拓了史学研究广阔的发展空间,对古文字学科发展同样产生深刻影响。安阳殷墟考古对甲骨文研究的影响就是典型例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28—1937年对殷墟进行持续考古发掘,先后出土有字甲骨共达28574片。[8]经科学发掘的殷商晚期都城遗迹和各类遗物,再现了甲骨文的埋藏环境、伴随出土物和坑位关系,新获甲骨文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研究资料,使得甲骨制作、占卜、断代、文字和内容解读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获得突破契机。根据殷墟考古所获,董作宾撰著《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十项标准”,把殷墟甲骨划分为“五个时期”,对甲骨文的科学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9]新中国成立后,殷墟考古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小屯南地、花园庄东地、小屯村中村南先后发现新甲骨。[10]根据考古新发现,考古学者、历史学者不断推进殷墟文化分期、甲骨文分期断代和相关研究走向深入,在“文武丁卜辞”、“历组卜辞”时代,以及甲骨文分组分类研究等方面都取得重要进展。[11]正是殷墟的考古发掘,促使甲骨文研究发展成为“甲骨学”这一古文字学的分支学科。[12]
古文字学研究的一些重要进展往往得益于考古新发现。如20世纪商周考古与青铜器铭文的大量发现,丰富了商周史研究的“直接史料”,青铜器与铭文研究发展成为古文字学的分支学科之一。[13]70年代以来,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器物铭文与湖北荆门包山、郭店楚简等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对战国文字研究的崛起并成为古文字学最为活跃的分支学科,发挥了巨大作用。[14]湖北云梦睡虎地、湖南长沙马王堆、山东临沂银雀山等多批次秦汉简帛资料的考古发现,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秦汉文字研究的历史,使简帛学成为古文字学又一个新的分支学科。[15]考古学新发现的各类古文字材料及其整理的研究成果,为古文字学发展和进步奠定了科学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文字学各研究领域的进步和分支学科的形成,都建立在20世纪以来古文字资料科学考古新发现的基础之上。
不仅如此,古文字学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切实提高了古文字释读和研究水平。如借鉴考古年代学、地层学等方法,为古文字资料的时代判定确立科学依据,有助于客观准确分析文字形体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进而演化出古文字动态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引进考古类型学方法,对古文字形体发展进行排谱和区域类型划分,揭示汉字形体演进的各个环节,使古文字形体结构的分析描写和发展谱系的建构趋向更加准确、科学。近年来,古文字结构、形体及其发展史研究所取得的一系列创新性成果,都得益于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吸收和运用。
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以文字、音韵、训诂见长,为古文字研究积累了丰厚资源;而古文字学的兴起和发展,则又极大拓展语言学特别是文字学的研究领域。古文字是汉字的早期形态,记录的是上古汉语。语言学者依据考古新发现的大量语料,运用语境、句法、语义、语用等语言学理论和分析方法释读古文字,探讨古汉语、文字学理论与汉字发展史有关问题,使语言学与古文字研究相得益彰。如唐兰从《说文解字》进入甲骨文、金文研究,首次提出建立作为文字学最重要部分的“古文字学”学科,并深入探讨古文字研究理论和方法;[16]杨树达以深厚的语言学、古文献学造诣,在甲骨文、金文字词考释方面多有所获;[17]于省吾利用古文字资料训释先秦文献,被誉为开创了训诂学的“新证派”,其古文字考释以精审著称,在甲骨文疑难字词考释方面成就巨大;[18]周法高、李孝定等全面搜集金文、甲骨文研究成果,主编《金文诂林》《甲骨文字集释》等,推进甲骨文、金文和汉字起源等问题的研究;[19]朱德熙、裘锡圭运用语言学科学方法,解决了许多古文字释读难题,其研究成果成为古文字学界的典范。[20]从语言学视角研究古文字,更加重视古文字形音义内在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深入辨析,探索古文字形体构造与汉字体系的发展规律,总结古文字释读理论和方法,自觉推进古文字研究学科化,为古文字学科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
从古文献学角度开展古文字材料整理、校勘和文本研究等工作,同样推进古文字学发展。以古文字材料整理为例,从早期罗振玉对甲骨文、金文资料的刊布和整理,到《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的编纂;从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孙海波《甲骨文编》、容庚《金文编(修订本)》相继问世,到各类古文字新材料文字编的适时编成;从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到各种类别古文字类纂的编撰,[21]以及各类古文字资料集释、字形表和目录文献的编纂出版,都是古文献整理研究方法与古文字学相结合而产生的成果。
以上表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古文献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共同促成古文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也决定了古文字学的交叉学科属性,以及所呈现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格局。
二、古文字研究与学科发展现状
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古文字研究与学科建设已进入快速进步、水平不断提高的新阶段。下面对近年来古文字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情况作一简略勾勒。[22]
(一)古文字资料整理和刊布有巨大进步,新出古文字材料整理出版更加适时,重新整理刊布一批旧藏材料,同时开展一些重要古文字材料的系统性、集成性整理研究。一是新出古文字材料整理刊布,大都信息记录详尽,图版清晰,文字释读也更加精审。近年来,除商周遗址、墓地、窖藏等持续有甲骨文、金文重要发现之外,诸侯方国金文和战国秦汉简牍的多批次发现尤其引人瞩目。考古发掘或收藏单位对这些新资料大都及时整理刊布,如山西曲沃晋侯、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山西翼城大河口霸国及绛县横水倗国等墓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等,[23]湖北江陵九店、荆门包山与郭店、河南新蔡葛陵等地考古新发现的楚简与上海博物馆、清华大学、安徽大学收藏的楚简等,[24]甘肃天水放马滩、湖南湘西里耶和岳麓书院以及北京大学收藏的秦简等,[25]湖北随州孔家坡、云梦睡虎地、荆州张家山及湖南沅陵虎溪山、成都天回老官山和北京大学收藏的汉简资料等。[26]
二是有关古文字资料收藏单位,利用新技术和手段对所藏资料进行更加科学的整理,出版或网上发布一批高质量、重新整理的古文字旧资料。以甲骨文为例,国内一些重要收藏单位,如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山东博物馆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等,都已开展或正在进行所藏甲骨文再整理工作。[27]这些单位对已著录或未著录的甲骨文旧藏开展新整理,体现新学术理念,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吸收古文字研究新成果,提供更加完整精确的甲骨文资料。除此之外,其他品类如金文、玺印、陶文等古文字资料旧藏,有关收藏单位也都有计划开展系统整理。重新整理刊布旧藏古文字材料,是深入推进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
三是对已发布的古文字资料开展集成性整理。这些整理工作及时汇总古文字研究新成果,使原来刊布的古文字资料整理和研究迈上新台阶。如甲骨文方面,新出《甲骨文摹本大系》《殷墟甲骨文分类与系联整理研究》《殷商子卜辞合集》等,[28]对已发布的甲骨文材料进行分组分类整理。在殷周金文和青铜器著录整理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前者对已出《殷周金文集成》进行订正增补、部分铭拓替换并增加释文,后者对中国近百年来出土青铜器进行分地区普查和著录。[29]战国秦汉简帛文字方面,《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秦简牍合集》《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等,[30]对楚简、秦简和马王堆帛书等重要材料再整理,汇集最新研究成果,极大提升了这几批材料的使用价值。集成性再整理的各类古文字材料,无论在材料搜罗广度、图版印制质量、释字水平上,都明显超过原有著录,为开展相关古文字深入研究提供了更好的资料。
(二)在古文字资料深度整理研究基础上编纂出版多种文字编、字形表、辞例类纂、逐字索引、考释集释等工具书。在文字编、字形表编著方面,从甲骨文到战国秦汉文字的重要材料,不仅编有文字编,而且同一种材料还编有多种,如《甲骨文字编》《新甲骨文编(增订本)》《新金文编》《战国文字编(修订本)》《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本)》《睡虎地秦简文字辞例新编》《秦文字编》《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全编》及《甲骨文字形表(增订版)》、“古汉字字形表系列”(包括商代、西周、春秋、战国、秦文字字形表5种)等。这些文字编、字形表吸收最新学术成果,及时反映古文字研究的新进展。[31]在深入整理基础上编纂的各类古文字辞例类纂、逐字索引工具书,对古文字学与相关学科研究也是有意义的工作,如《殷墟甲骨文辞类编》《商周金文辞类纂》《楚简帛逐字索引(附原文及校释)》《秦简逐字索引(增订本)》等。[32]古文字集释类著述,全面汇纂各家古文字考释成果,不同意见兼收并蓄,既为古文字研究者节省许多检索时间,又能体现古文字考释的学术发展历史,对推进古文字研究大有裨益。近出这类工具书有:《古文字诂林》《甲骨文字诂林补编》《商周金文辞汇释》《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集释》等。除此之外,还出版一些综合性或专题性工具书,如梳理证说古文字发展谱系的《古文字谱系疏证》,以及集纂古文字通假材料的《古文字通假字典》《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等。[33]以上古文字工具书的编纂,跟踪古文字材料刊布和研究进程,注意吸收古文字研究最新成果,切合古文字研究的时代需求,为研究者提供极大便利。
(三)古文字释读水平全面提高,古文字材料专题研究更加深入,古文字理论综合研究有所进展。各类古文字资料新发现,加速古文字释读水平不断提高,古文字中新见字和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疑难字词考释取得突破,产生一批较为重要的古文字释读新成果。如刘钊释“害”与“役”、陈剑释“徹”、蒋玉斌释“蠢”、王子杨释“阱”与“丽”、周忠兵释“仆臣臺”之“臺”、郭永秉释“要”,以及赵平安、陈剑等发表多篇考释古文字疑难字词的文章。[34]以上一些考证成果先后获得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一、二等奖奖励。[35]对古文字材料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一批值得重视的新成果,涉及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形体、结构、字用、文例等重要现象,以及内容释读和相关问题讨论,材料整理全面系统,分析考察细致深入,提升了古文字释读和研究的整体水平。如王子杨《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孙亚冰《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例研究》、谢明文《商代金文研究》、陈斯鹏《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周波《战国时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研究》、吴振武《古玺文编校订》、肖毅《古玺分域研究》、陈昭容《秦系文字研究:从汉字史的角度考察》、李春桃《古文异体关系整理与研究》等。[36]在总结新材料、新释字基础上,古文字学理论综合研究和知识体系建构也有所进展,出版《古文字构形学》《古汉字发展论》《汉字学论稿》《形体特点对古文字考释重要性研究》等理论研究论著。围绕知识体系建构的教材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古文字学理论综合研究成果,如黄德宽《古文字学》、冯时《中国古文字学概论》等。[37]最近,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著《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程》正式出版,[38]也是古文字综合理论研究的一项新成果。
(四)古文字研究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呈现加快趋势。历史学方面,发表了一批利用古文字材料开展史学专题研究的论著,如章秀霞等《花东子卜辞与殷礼研究》、李发《甲骨军事刻辞整理与研究》、刘新民《甲骨刻辞羌人暨相关族群研究》、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李守奎《古文字与古史考——清华简整理研究》、杜勇《清华简与古史探赜》、吴良宝《战国楚简地名辑证》、罗小华《战国简册中的车马器物及制度研究》、贾连翔《出土数字卦文献辑释》、杨博《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程浩《出土文献与郑国史新探》。[39]这些研究利用甲骨文、商周金文和战国秦汉等古文字材料,探讨上古政治、军事、礼制、职官、地理和名物等方面的历史问题,开拓了历史学与古文字学相结合的研究领域。
语言学研究方面,以古文字材料为语料研究上古汉语有关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产生多部专题研究论著,如齐航福《殷墟甲骨文宾语语序研究》、武振玉《两周金文动词词汇研究》、杨怀源等《两周金文用韵考》、张玉金《出土战国文献虚词研究》、姚振武等《简帛文献语言研究》、张富海《古文字与上古音论稿》等。[40]上述论著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分析古文字资料中的语言现象,在上古语法、词汇、文字和音韵等研究方面有新收获,对依据语言规则释读古文字也产生积极影响,提升古文字研究的科学水准。
古文献学研究方面,一方面运用文献学研究手段和方法对古文字资料进行系统整理,为古文字研究奠定文本基础,这是古文献学对出土文献研究的主要贡献;另一方面对出土文献呈现的各种语言文字和文本现象开展相关问题研究,产生了一批古文献学与古文字研究交叉融合的新成果。如冯胜君《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徐富昌《简帛典籍异文侧探》、贾连翔《战国竹书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为中心》、程浩《有为言之:先秦“书”类文献的源与流》等;围绕战国秦汉简等出土文献的编连、缀合、校读方面,发表许多专题研究论著。[41]这些研究涉及出土简本文献制作与形制、地域特点、流传方式,以及整理过程中的编连、文字形体和简文异文及内容校订等方面,出土文献已发展成为古文献学研究异军突起的新领域。
(五)古文字研究对智能技术的积极尝试和初步应用,已悄然推动古文字数字化进程。古文字研究与智能技术结合是跨越人文和科技的一种学科交叉,为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带来新机遇。根据2023年“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年度总结,有关工程建设单位积极推动古文字数字化,已取得一些初步成果。如清华大学开展计算甲骨学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并将启动建设计算古文字学实验室。[42]吉林大学在人工智能与古文字交叉领域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开发出“吉金识辨·青铜器智能断代与辨类”程序,并建成青铜器数据库。[43]复旦大学发布“缀玉联珠”甲骨缀合信息库,可便捷查检相关信息。[44]首都师范大学与微软亚洲研究院合作研发基于自监督学习的甲骨文校重助手Diviner,开创人工智能与甲骨文专家协作(AI+HI)整理甲骨文的新范式。[45]此外,还有一些高校和研究单位在甲骨文等古文字信息处理和技术研发方面也开展了积极尝试,如甲骨文发现地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师范学院获批建立教育部甲骨文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着力打造“殷契文渊”甲骨文大数据平台。这些工作虽然还只是应用智能技术研究古文字取得的初步成果,但有关研究单位对智能技术跨学科研究的重视和布局,为古文字研究与学科建设展现出令人期待的前景。[46]
(六)古文字学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得到加强,发展环境显著改善。1978年10月,在吉林大学召开的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学者呼吁尽快改变古文字科研工作的落后状况,将研究队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作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47]20世纪80年代全面恢复研究生招生后,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在不同学科下设立古文字学方向培养研究生。经过40多年的努力,古文字学研究队伍状况得到显著改变。目前,从事古文字学研究和教育的学者,基本上是这个阶段培养的研究生。2020年,教育部启动实施古文字学本科人才“强基计划”,部分重点高校开始招收古文字学本科生,建立起本科到研究生相贯通的古文字学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48]高等学校“强基计划”古文字学本科招生专业(方向)的设立,既加强古文字学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的相互衔接,又对古文字学研究生教育提出更高要求。清华大学基于古文字学科发展新趋势,适时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国内首个古文字学一级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从本科到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的不断完善,古文字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地位得以确立,人才培养得到进一步加强。适应古文字学培养和科研之需,古文字研究人才队伍建设也取得明显成效,一批优秀青年学者快速成长为学术骨干,他们代表古文字学发展的未来。2020年以来,参与“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建设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并分别建立起本单位古文字研究专门机构,创办《出土文献》等多种古文字研究学术期刊(集刊)、交叉学科实验室和工作坊,加大对古文字研究的经费支持,古文字学发展环境大为改善。
(七)古文字学领域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外国学者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给中国学者以有益启发,开拓古文字学研究的国际视野,同时,也扩大中国古文字学的国际传播和影响力。近年来,国外学者依据古文字新出资料研究早期中国文明、文本和语言文字等问题,取得不少有影响的成果,如美国艾兰(Sarah Allan)、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柯马丁(Martin Kern)、顾史考(Scott Cook),以色列尤锐(Yuri Pines),英国麦笛(Dirk Meyer),日本林巳奈夫、工藤元男等人出版有关著作。[49]他们的代表性著作多被介绍到国内,研究方法和学术见解受到中国古文字学者的重视。通过国际学术交流,中外学者加强彼此的沟通理解,进而推动在古文字学领域实施一些重要的合作项目,如夏含夷组织国际学者与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合作开展清华简的研究和英译工作,出版英文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与英译”丛书,向海外展示清华简这一先秦文献的重大发现。[50]中外学者在古文字学领域的合作交流,有助于提升中国古文字学研究水平,更好推进中国古文字学走向世界。
综上所述,古文字研究与学科建设近年来取得重要进展,无论古文字材料整理、工具书编纂,还是文字考释、专题研究等方面成果都相当突出,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国际交流合作也有较大进展。总体上看,古文字学已进入研究水平全面提升、学科建设日益加强的新阶段。
三、古文字学交叉学科建构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古文字研究和学科建设虽然呈现全面进步、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但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建构,还面临一些有待破解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薄弱环节。
其一,在古文字材料整理方面,新发现古文字资料整理研究任务艰巨,考古发掘单位古文字研究力量大都不足,一些新材料还不能及时整理利用;收藏单位开展所藏古文字资料再整理,对重新整理必要性的论证、整理标准和规范的确立,以及整理队伍的组织等方面,还缺乏统一规定和有效统筹,存在难以保证整理质量和水平、重复整理出版、文字文物安全等隐忧;古文字材料数字化工作处于初级阶段,有些单位或个人虽然在古文字数字化工作方面花费不少力气,但由于古文字释读水平不高,或信息技术水平较低,以至成效不大,甚至做无用功。古文字资料的全面、高水平整理,是深入推进古文字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应引起重视。
其二,在古文字考释方面,甲骨文未识字和其他古文字材料中疑难字词的考释成为瓶颈,寻求古文字未识字、疑难字词考释的突破,依然是古文字释读面临的基本任务。古文字考释目前呈现两极化倾向,既有论证充分、结论精准的古文字考释优秀成果不断问世,又有一些考释文章不能遵循古文字释读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甚至刻意标新立异,以至于鱼目混珠,徒添混乱。
其三,在古文字学理论研究方面,综合研究较为薄弱,系统总结、深入揭示古文字形体构造与发展规律的有分量成果较少,而追逐新出古文字材料的碎片化研究则成为一时之尚;对一些重大的古文字学基础理论问题关注不够,研究进展有限。如汉字起源与早期中华文明形成问题、殷墟甲骨文之前的汉字问题、夏商周之间文字传承和发展问题、先秦文字与上古汉语关系问题、古文字历史文化功能的科学评价问题等。这些古文字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关系到古文字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标志,汉字何以成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并富有生命力的古典文字体系,以及汉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深入探索和古文字历史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
其四,在交叉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虽然近年来古文字学科交叉研究取得一批新成果,但从多学科交叉研究转化为具有明确内涵规定的新兴交叉学科建设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目前不同学科学者的研究,只是延续多学科参与研究古文字的既往路径,他们从事的教学科研工作依然归属于不同学科,在使用相同类型古文字资料开展有关问题研究时往往各有千秋,打上不同学科的鲜明烙印,还不是真正意义上古文字学交叉学科的研究。与老一辈学者相比,年轻学者教育背景导致其文史知识积累不足,由不同学科进入古文字研究领域后,有时往往因古文字基础不牢而捉襟见肘;有些虽古文字基础较好,但立足于交叉学科来开展相关问题研究时又显得力不从心。跨越人文与科学技术界域,真正发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在古文字交叉研究中的优势,需要能够贯通信息技术与古文字知识的高水平交叉学科人才,这类人才目前最为紧缺。总体来看,古文字学还处于学科交叉向交叉学科转型的初级阶段,如何界定古文字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内涵和属性,如何培育一支古文字学交叉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队伍,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建构新兴交叉古文字学科面临的有关问题和薄弱环节,与古文字学科形成历史、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密切相关。新形势下,古文字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要立足于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高度来着力推进,并努力探求解决相关问题、加强薄弱环节之道。
首先,要加强新兴交叉学科视域下的古文字学理论综合研究,聚焦古文字研究若干重大理论问题,推进古文字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古文字资料、研究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加强古文字学理论综合研究,既是古文字研究弥补薄弱环节、不断走向深入的必然要求,又是新兴交叉学科视域下建构古文字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任务。百余年来,多学科学者共同参与促成了现代古文字学的形成和发展,多学科交叉和融合在古文字学科发展历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为古文字学发展成为新兴交叉学科奠定坚实基础。但是,由于不同学科各有学科界域和研究任务,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古文字学,始终没能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完全确立独立的学科地位,古文字学理论综合研究薄弱正是这种状况的体现。古文字学作为一级交叉学科建设,加强古文字学理论研究显得尤为必要。一方面,要探讨作为交叉学科的古文字学科属性、学科内涵、研究任务、基本理论和方法等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立足于交叉学科建设,研讨如何实现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古文献学等学科与古文字学科更深度的交叉融合;另一方面,要对古文字学若干重要问题开展更加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如汉字起源、古文字形体结构及其发展演变、字际关系和字词关系、功能与性质、释读理论与方法,以及汉字传承和传播、汉字历史文化价值等问题的研究,要以古文字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取得的成果,为古文字学交叉学科的发展奠定科学基础。与此同时,全面总结百余年来古文字学科建设的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行古文字学理论创新和学科知识的系统化整合,进而建构中国古文字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应作为古文字学交叉学科建设的一项奠基性工作。古文字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将为古文字学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水平的提高奠定理论基础。
其次,要加快培养具有交叉学科学术视野、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的古文字学后备人才。古文字学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对古文字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决定性影响。古文字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主要任务是:在科学整理研究各种出土古文字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古汉字形体构造的理论和方法,揭示汉字起源和发展演变规律,考辨未释古文字的形音义,总结古汉字运用遵循的基本规则,进而阐释古汉字形体构造及其发展演进的历史文化动因,探索汉字与中华文明形成、发展和传播的深层关系,为传承弘扬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提升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夯实学术根基。古文字学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决定其需要融合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古文献学等多学科知识,并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上,建构自身学科和知识体系,形成符合古文字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理论和方法。[51]交叉学科门类下的古文字学科建设,必然要突破已有学科界域,将有关学科知识进行有机融合再造,建立一套新的培养方案、课程和知识体系,以培养适应交叉学科需求的拔尖创新人才。这是古文字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一次重要改革。只有花大力气加快培养具有交叉学科学术视野、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的古文字学卓越后备力量,才能为古文字研究和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将古文字学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新兴交叉学科。
最后,要把握智能技术革命的机遇,推进信息技术、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在古文字学交叉学科建设中的运用,探索建立人文学科与智能技术交叉融合的“计算古文字学”研究方向。一是依托信息技术改变古文字资料存储和利用方式,创建古文字资料收集整理的统一规范,整合已经完成的各类古文字材料整理成果,将数量巨大、内容庞杂的古文字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为古文字研究全面快捷获取、使用各种古文字资料提供便利。二是引入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等计算工具,整合已有的各类工具书,汇集各种古文字研究有价值的成果,建立各类古文字资源数据库平台,构建古文字知识图谱,让人工智能系统成为古文字学者的得力助手。三是利用人工智能探研古文字知识新的生产方式,创新和重构数字化条件下的古文字研究范式,为适应数字化时代需要、全面提升古文字整理研究和阐释水平注入强劲动力。虽然智能技术在古文字学领域运用尚处于摸索阶段,但古文字学交叉学科建设与智能技术的结合则是必然趋势,在二者深度融合的基础上创立“计算古文字学”新交叉学科方向将成为可能。[52]尽管数字技术革命为古文字学交叉学科发展描绘出令人乐观的前景,但是要实现古文字学与智能技术深度融合还要经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而且再先进的人工智能也只是古文字研究的赋能工具,对古文字研究和学科建设未来起决定作用的,最终还是要依靠具有交叉学科视野和创新能力的古文字学者。
冷门不冷,绝学不绝。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征程中,古文字研究和学科发展迎来了最好的时代环境,依托百年来形成的经验和学术积累,针对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通过创新理论、培养人才和数字化工具变革等举措,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古文字研究和学科建设必将大有可为!
注释
[1]学界对古文字学有“广义”与“狭义”的分别,裘锡圭认为,“广义的古文字学既包括对古文字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对各种古文字资料的研究……狭义的古文字学主要以古文字本身为对象,着重研究汉字的起源,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字形所反映的本义以及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古文字学简史》,《裘锡圭学术文集》第3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90页)。根据此区分,本文所讨论的属于“广义的古文字学”。
[2]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从古文字学科形成和发展角度,主要考察古文字学的历史发展与新时期以来我国古文字学的情况,不是对古文字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全面总结。关于较为全面的古文字研究历史,从“广义”或“狭义”古文字学角度进行总结的相关论著不少。如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王宇信等:《甲骨学发展12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赵诚:《二十世纪金文研究述要》《二十世纪甲骨文研究述要》上、下册,太原:书海出版社,2003、2006年;裘锡圭、沈培:《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字学》,《裘锡圭学术文集》第4卷;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陈剑:《近二十来年的古文字学鸟瞰》,中西书局组编《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第312—330页。
[3]“直接史料”“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史料,“间接史料”“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史料。参见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民族与古代中国史》附录3,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21—450页。
[4]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8卷《观堂集林》,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5]郭沫若:《卜辞通纂》,东京:文求堂书店,1933年影印本;《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金文丛考》,东京:文求堂书店,1932年影印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6]胡厚宣是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华书局,1978—1983年)的总编辑,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对殷商史有关问题开展专题研究,并撰写一系列重要论著。参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四集,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1945、1946年。
[7]参见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集》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唐兰先生金文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于省吾主编,姚孝遂按语编撰:《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张政烺:《甲骨金文与商周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8]包括河南省博物馆发掘队1929—1930年两次发掘所获有字甲骨3656片。参见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第44页。
[9]董作宾作为殷墟考古的参与者还撰写有《新获卜辞写本后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1929年;《甲骨文研究的扩大》,《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1930年;《大龟四版考释》,《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1931年。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
[11]这方面代表性研究成果,如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4、5期;李学勤:《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1981年第5期;《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等编:《古文字研究》第18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6—30页;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四川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3—321页;林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山西省文物局等编:《古文字研究》第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1—154页;萧楠:《甲骨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萧楠”为小屯南地甲骨整理小组刘一曼、温明荣、曹定云和郭振禄的共同笔名,取自“小南”(小屯南地)的谐音。
[12]参见刘一曼:《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
[13]关于考古发现的金文资料及金文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4年;刘雨等:《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朱凤翰:《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等等。
[14]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文物》1979年第1期;张政烺:《中山王 壶及鼎铭考释》《中山国胤嗣
壶及鼎铭考释》《中山国胤嗣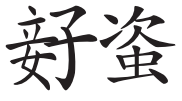 壶释文》,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08—246页;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
壶释文》,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08—246页;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
[15]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2010年;王辉等:《秦文字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李均明等:《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1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16]唐兰的古文字研究著作,除《古文字学导论》《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之外,还有《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殷虚文字记》《甲骨文自然分类简编稿本》等多种(《唐兰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17]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 卜辞琐记》,北京:中国科学院,1954年;《耐林庼甲文说 卜辞求义》,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年;《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积微居金文说》,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18]于省吾:《双剑誃尚书新证》《双剑誃诗经新证》《双剑誃易经新证》《双剑誃诸子新证》《双剑誃殷契骈枝》《双剑誃殷契骈枝续编》《双剑誃殷契骈枝三编》《甲骨文字释林》,《于省吾著作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9]周法高等编纂:《金文诂林》,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4年;周法高编撰:《金文诂林补》,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年;周法高等编著:《金文诂林附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7年;李孝定编述:《甲骨文字集释》,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金文诂林读后记》,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年;《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
[20]朱德熙:《朱德熙古文字论集》,裘锡圭、李家浩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
[21]郭沫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商承祚编:《殷墟文字类编》,决定不移轩刻本,192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甲骨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该版由孙海波《甲骨文编》改订而成;容庚编著:《金文编(修订本)》,张振林、马国权摹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22]本文对古文字研究现状的观察,主要选取21世纪以来公开发表的部分代表性成果,没有公开发表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皆不予介绍。关于目前古文字学研究的总体情况,可参见陈剑:《近二十来年的古文字学鸟瞰》,中西书局组编《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发展》,第314—316页。
[23]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邹衡主编:《天马—曲村1980—1989》第1—4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湖北省博物馆等编:《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编著:《霸金集萃: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青铜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倗金集萃: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出土青铜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2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新蔡葛陵楚墓》,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12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1—14册,上海:中西书局,2011—2024年;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编,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二),上海:中西书局,2019、2022年。
[2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贰)(叁),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2017、2024年;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第1—7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2022年;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第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2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编:《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睡虎地西汉简牍·质日》,上海:中西书局,2023年;荆州博物馆编,彭浩主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三三六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年;天回医简整理组编:《天回医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015年。
[27]如国家图书馆2018年获批“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整理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面整理所藏甲骨,拍摄高清数码照片网络发布,为学界提供更全面的资料。另参见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甲骨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马衡卷、谢伯殳卷),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濮茅左编著:《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旅顺博物馆编著,宋镇豪等主编:《旅顺博物馆所藏甲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宋镇豪等编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甲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李钟淑等著,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吕静主编,葛亮编著:《复旦大学藏甲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吴振武主编:《吉林大学藏甲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28]黄天树主编:《甲骨文摹本大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彭裕商主编:《殷墟甲骨文分类与系联整理研究》,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23年;蒋玉斌编著:《殷商子卜辞合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20年。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北京: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8年。这类著录材料还有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016、2020年;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张天恩主编:《陕西金文集成》,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年;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编著,徐天进、段德新主编:《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商周青铜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山西考古研究院编:《山西出土青铜器全集·闻喜酒务头卷》,太原:三晋出版社,2022年;山东省博物馆编:《山东金文集成》,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张振谦编著:《齐系金文集成·鲁邾卷》《齐系金文集成·齐莒甲卷》,北京:学苑出版社,2017、2018年。
[30]武汉大学简帛中心等编,陈伟、彭浩主编:《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2024年;武汉大学简帛中心等编,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湖南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2024年出版修订本。
[31]李宗焜编著:《甲骨文字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刘钊主编:《新甲骨文编(增订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董莲池编著:《新金文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汤馀惠主编:《战国文字编(修订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滕壬生编著:《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本)》,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徐富昌:《睡虎地秦简文字辞例新编》上、下,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王辉主编:《秦文字编》,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刘钊主编:《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全编》,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沈建华、曹锦炎编著:《甲骨文字形表(增订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黄德宽主编,徐在国副主编:《商代文字字形表》《西周文字字形表》《春秋文字字形表》《战国文字字形表》《秦文字字形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此外,还有陈斯鹏等编著:《新见金文字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刘志基主编:《古文字构形类纂·金文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3年;吴国升编著:《春秋金文全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汤志彪编著:《三晋文字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张振谦编著:《齐鲁文字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年;张振谦编著:《燕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23年;李守奎等编著:《包山楚墓文字全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玖)文字编》,上海:中西书局,2014、2017、2020年;徐在国编:《传抄古文字编》,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方勇编著:《秦简牍文字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陈松长等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柒)文字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2023年;蒋伟男编著:《里耶秦简文字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18年;张守中编撰:《张家山汉简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32]陈年福编著:《殷墟甲骨文辞类编》,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21年;张桂光主编:《商周金文辞类纂》,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张显成主编:《楚简帛逐字索引(附原文及校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张显成主编:《秦简逐字索引(增订本)》,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其他如齐航福、章秀霞编著:《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刻辞类纂》,北京:线装书局,2011年;李霜洁编著:《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刻辞类纂》,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
[33]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2004年;何景成编撰:《甲骨文字诂林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董莲池编著:《商周金文辞汇释》,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曾宪通、陈伟武主编:《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俞绍宏、张青松编著:《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集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王辉编著:《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白于蓝编著:《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
[34]刘钊:《甲骨文“害”字及从“害”诸字考释》,宋镇豪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新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6—115页;《释甲骨文中的“役”字》,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3—67页;陈剑:《释甲骨金文的“徹”字异体——据卜辞类组差异释字之又一例》,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19页;蒋玉斌:《释甲骨金文的“蠢”兼论相关问题》,《复旦学报》2018年第5期;王子杨:《释甲骨文中的“阱”字》,《文史》2017年第2辑;《甲骨金文旧释“競”的部分字当改释为“丽”》,《出土文献》2020年第1期;周忠兵:《出土文献所见“仆臣臺”之“臺”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0本第3分,2019年;郭永秉:《谈古文字中的“要”字和从“要”之字》,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古文字研究》第28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08—115页;赵平安:《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续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018年;陈剑:《甲骨金文考释论集》,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近年来,古文字考释新成果数量多、质量高,对不少未识字和疑难字词提出新释,以上所引,仅为部分中青年学者的代表性成果。
[35]2016年10月,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同意,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关于征集评选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的奖励公告》,组织实施甲骨文释读成果专项奖励计划,面向海内外公开征集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并予以奖励。2018年6月和2024年1月分别公布了第一、二批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评选结果,蒋玉斌、陈剑、周忠兵、王子杨等上述论文分别获得一、二等奖。
[36]王子杨:《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孙亚冰:《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谢明文:《商代金文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陈斯鹏:《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周波:《战国时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12年;吴振武:《古玺文编校订》,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肖毅:《古玺分域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18年;陈昭容:《秦系文字研究:从汉字史的角度考察》,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3年;李春桃:《古文异体关系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这类成果还有萧毅:《楚简文字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天虹:《楚国铜器与竹简文字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徐在国:《上博楚简文字声系(一—八)》,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董珊:《吴越题铭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张峰:《楚文字讹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禤健聪:《战国楚系简帛用字习惯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周波:《战国铭文分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张振谦:《齐系文字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孙刚:《东周齐系题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孙合肥:《战国文字形体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李松儒:《清华简字迹研究》,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23年。
[37]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黄德宽等:《古汉字发展论》,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李守奎:《汉字学论稿》,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刘洪涛:《形体特点对古文字考释重要性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黄德宽:《古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冯时:《中国古文字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38]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撰:《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教程》,上海:中西书局,2024年。
[39]章秀霞等:《花东子卜辞与殷礼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李发:《甲骨军事刻辞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刘新民:《甲骨刻辞羌人暨相关族群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李守奎:《古文字与古史考——清华简整理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杜勇:《清华简与古史探赜》,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吴良宝:《战国楚简地名辑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罗小华:《战国简册中的车马器物及制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贾连翔:《出土数字卦文献辑释》,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杨博:《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程浩:《出土文献与郑国史新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此外,还有刘凤华:《殷墟村南系列甲骨卜辞整理与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单育辰:《甲骨文所见动物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商艳涛:《西周军事铭文研究》,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罗运环:《出土文献与楚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王伟:《秦玺印泥职官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程燕:《战国典制研究——职官篇》,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8年;吴毅强:《晋铜器铭文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
[40]齐航福:《殷墟甲骨文宾语语序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武振玉:《两周金文动词词汇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杨怀源等:《两周金文用韵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张玉金:《出土战国文献虚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简帛文献语言研究》课题组:《简帛文献语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张富海:《古文字与上古音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其他成果还有王晓鹏:《甲骨刻辞义位归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杨怀源:《西周金文词汇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7;李明晓:《战国楚简语法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伊强:《秦简虚词及句式考察》,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张玉金:《出土战国文献动词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此外,朱歧祥《亦古亦今之学——古文字与近代学术论稿》(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季旭昇《季旭昇学术论文集》第1—5册(新北: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2年)等,收录作者关于甲骨、金文与出土战国文献字词考释等论文,对相关语言文字释读提出一些值得重视的意见。
[41]冯胜君:《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徐富昌:《简帛典籍异文侧探》,台北:“国家”出版社,2006年;贾连翔:《战国竹书形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为中心》,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程浩:《有为言之:先秦“书”类文献的源与流》,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刘乐贤:《战国秦汉简帛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陈剑:《战国竹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董珊:《简帛文献考释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42]李霜洁等:《数智增强的古文字文献新整理:以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刻辞为例》,杜晓勤主编:《中国古典学》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67—86页;蒋玉斌等:《人工智能引导人类直觉产生的甲骨新缀十组》,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1063,访问日期:2023年10月12日;蒋玉斌等:《人工智能引导人类直觉产生的甲骨新缀第11—20组》,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1067,访问日期:2023年11月12日;李霜洁:《人工智能引导人类直觉产生的甲骨新缀第21—30组》,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1105,访问日期:2024年1月20日;《人工智能引导人类直觉产生的甲骨新缀第31组——续补殷墟卜辞中的贞人网络》,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1109,访问日期:2024年2月4日;《人工智能引导人类直觉产生的甲骨新缀第32—40组》,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1111,访问日期:2024年2月19日。
[43]李春桃等:《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古文字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2期;李春桃等:《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青铜鼎分期断代研究》,《出土文献》2023年第3期;Zhou Rixin et al.,“Multi-Granularity Archaeological Dating of Chinese Bronze Dings Based on a Knowledge-Guided Relation Graph,” in Proceedings of the IEEE/CVF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2023, pp. 3103-3113; Li Chun tao et al., “AI Mobile Application for Archaeological Dating of Bronze Dings,” DOL: https://doi.org/10.48550/arXiv. 2401,01002; Chi Yang, et al.,“ZiNet: Linking Chinese Characters Spanning Three Thousand Years,”in Fin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CL 2022, 2022, pp. 3061-3070.
[44]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缀玉联珠”甲骨缀合信息库,http://www.fdgwz.org.cn/ZhuiHeLab/Home.
[45]武智融等:《人工智能在甲骨文重片整理中的应用》, https://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7264.html,访问日期:2022年11月30日;微软亚洲研究院:《人工智能开启甲骨文整理研究新范式》,https://www.msra.cn/zh-cn/news/features/oracle-bone-script,访问日期:2022年11月22日。
[46]本文关于古文字与智能技术研究有关成果的介绍及相关论述,得到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霜洁博士的帮助,谨此致谢!
[47]姚孝遂:《古文字研究工作的现状及展望》,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22页;《迅速改变古文字科研工作的落后状况——一些古文字学家就此问题提出建议》,《文汇报》1979年1月24日。
[48] “强基计划”指教育部推行的基础学科本科招生改革(试点)计划,主要目的是选拔培养有助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的基础学科拔尖人才。该计划自2020年起在部分高校试点,“古文字学”被列入计划之中。
[49]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增订版)》,汪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新译本)》,余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增订版)》,张海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增订版)》,杨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湮没的思想——出土竹简中的禅让传说与理想政制》,蔡雨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夏含夷:《古史异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重写中国古代文献》,周博群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柯马丁:《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刘倩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顾史考:《郭店楚简先秦儒书宏微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上博等楚简战国逸书纵横览》,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Yuri Pines, “Xinian and Zhou Historiography,” Zhou History Unearthed: The Bamboo Manuscript Xinian and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37-67;麦笛:《竹上之思:早期中国的文本及其意义生成》,刘倩译,香港:中华书局,2021年;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共3卷,广濑薰雄、近藤晴香译,郭永秉润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2019年、2022年;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广濑薰雄、曹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50]该丛书由黄德宽与夏含夷总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计划出版18卷,2023年已出版第1卷《〈逸周书〉诸篇》(夏含夷著译),2024年出版第2卷《〈尚书〉诸篇》(夏含夷著译)、第3卷《〈伊尹〉诸篇》(周博群著译)、第6卷《〈郑武夫人规孺子〉诸篇》(武致知著译)。
[51]关于古文字学作为交叉学科的主要任务等表述,出自笔者主持完成的清华大学古文字学一级学科论证报告,该报告已在一定范围内公开。202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批准清华大学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古文字学一级学科。
[52]莫伯峰:《“计算古文字学”正在路上》,《光明日报》2022年10月30日,第5版。
原载《历史研究》2024年第12期,引用请据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