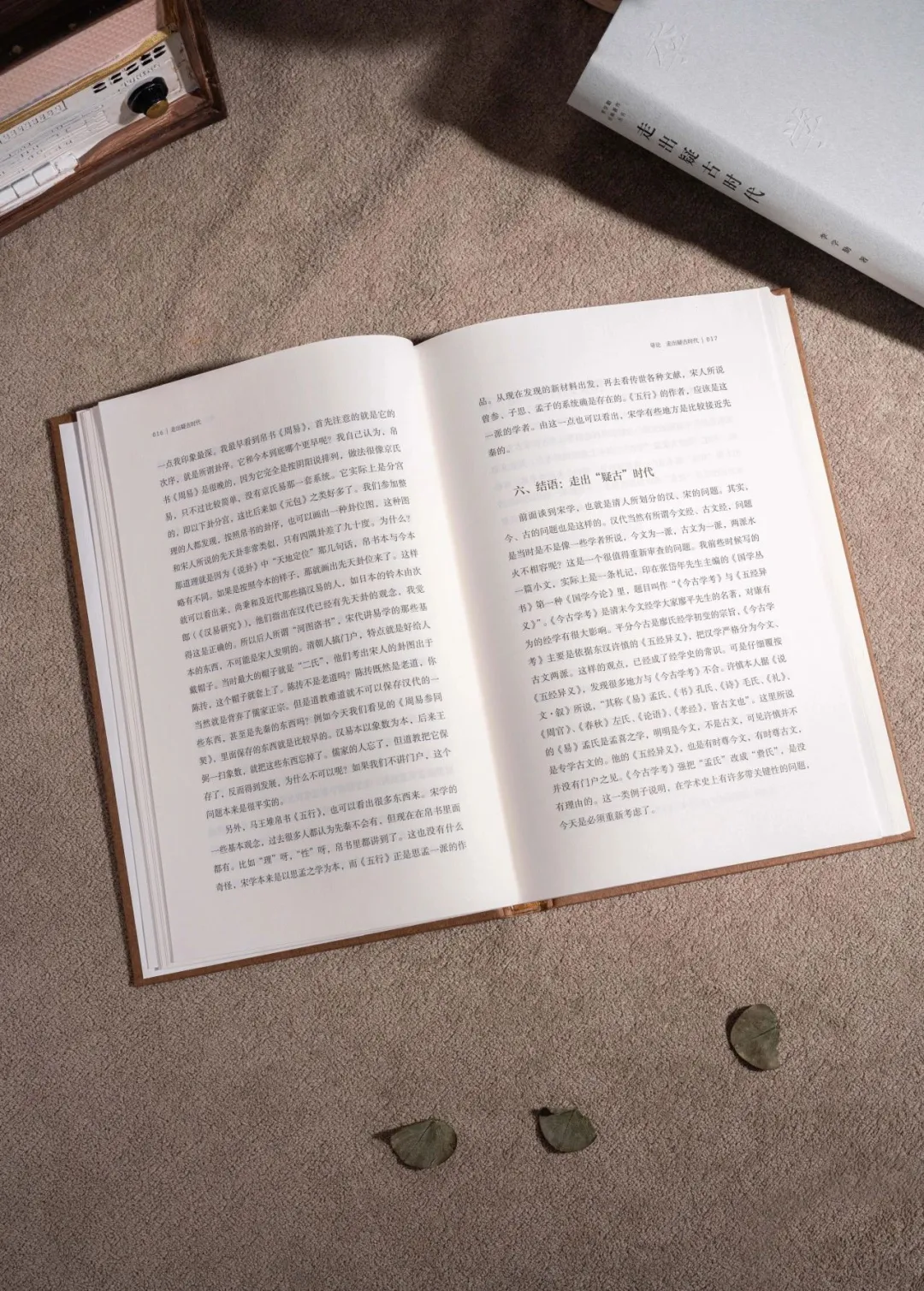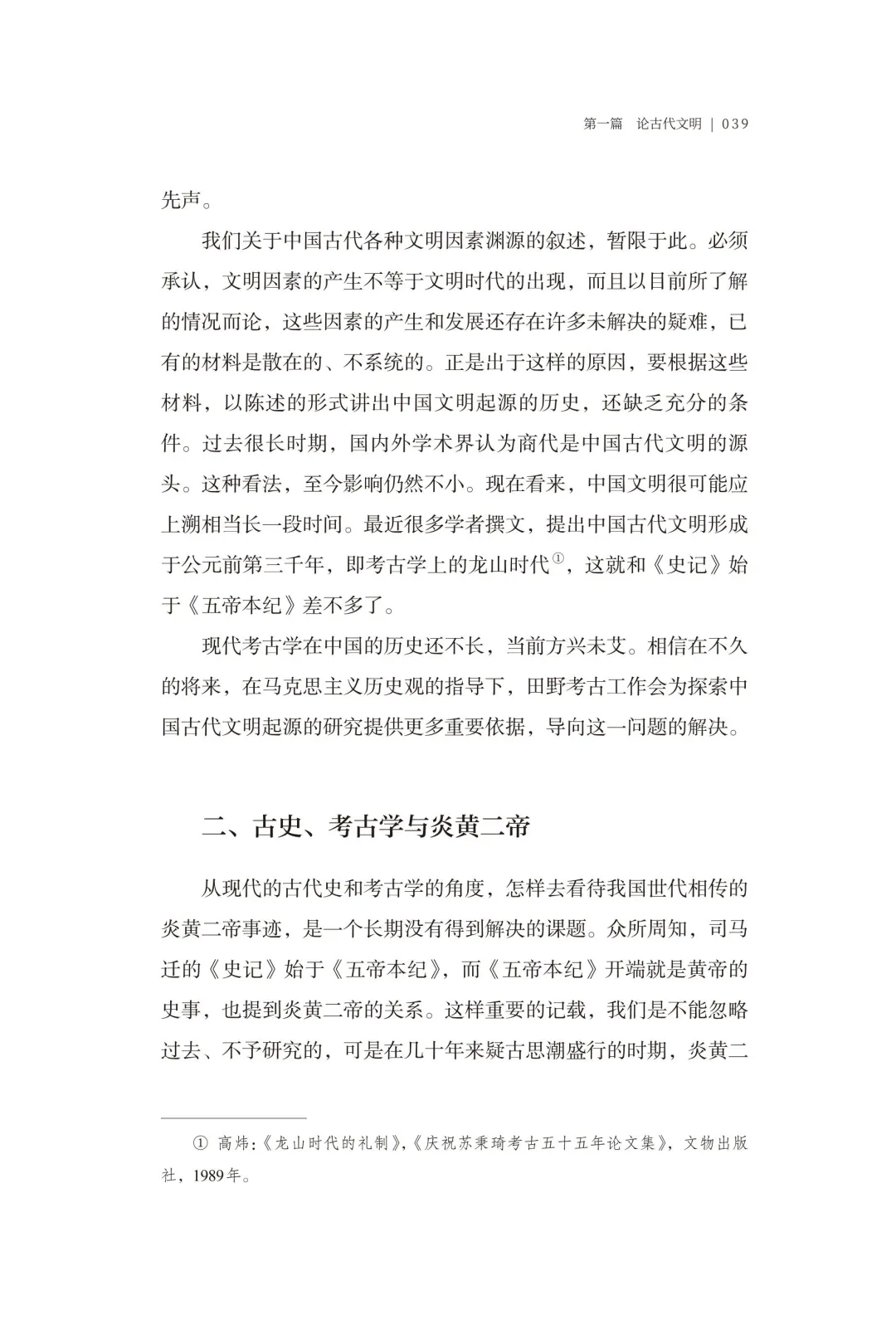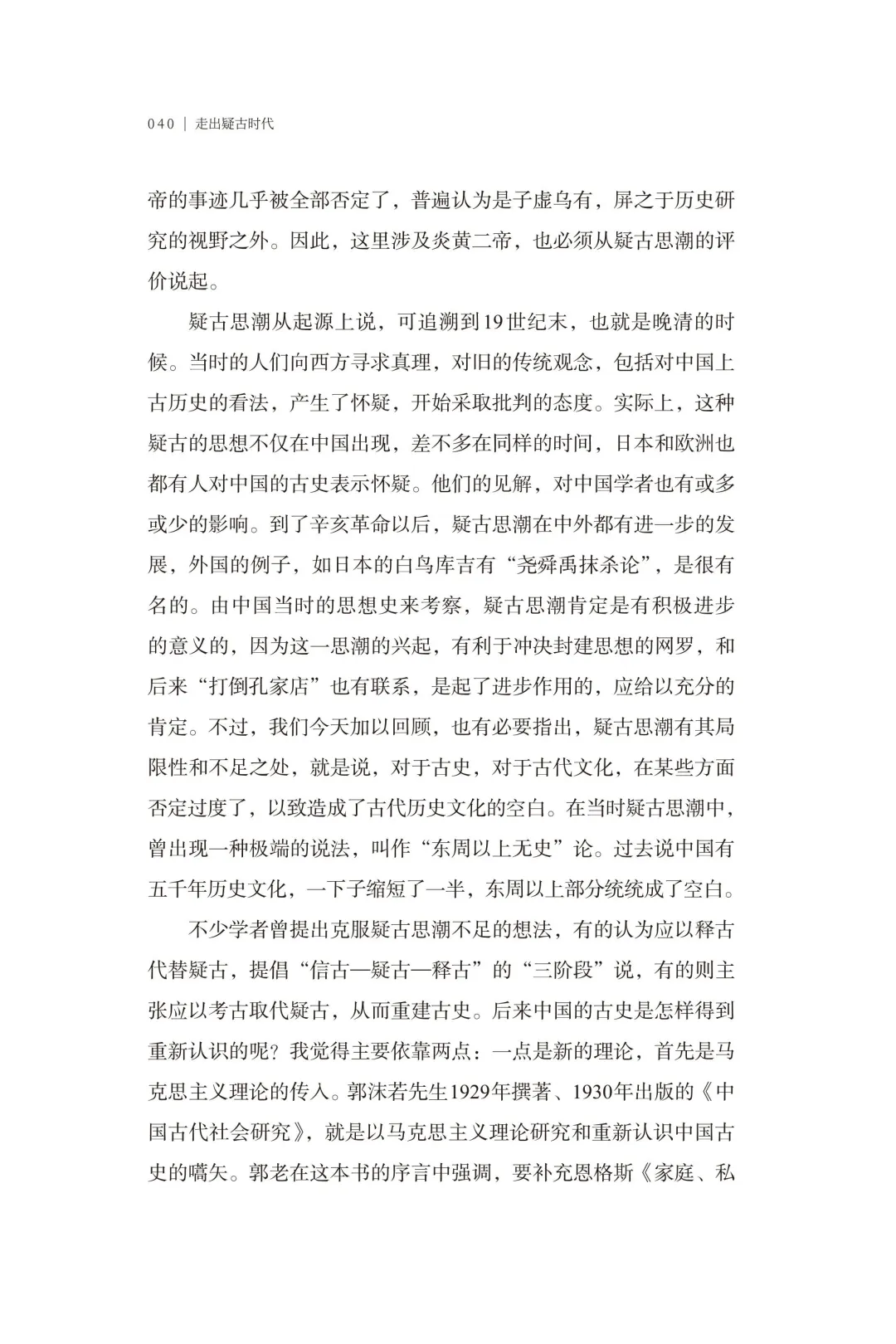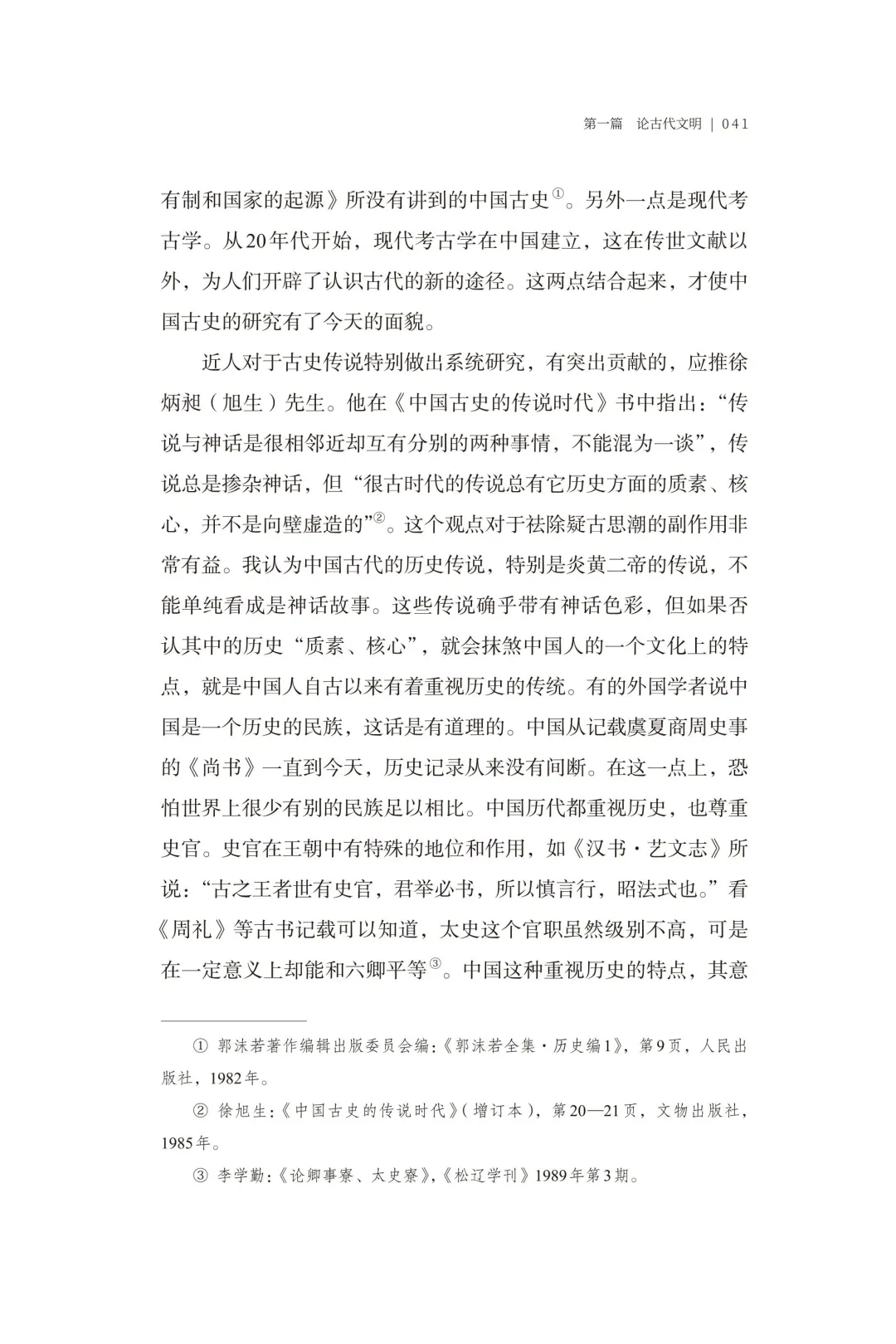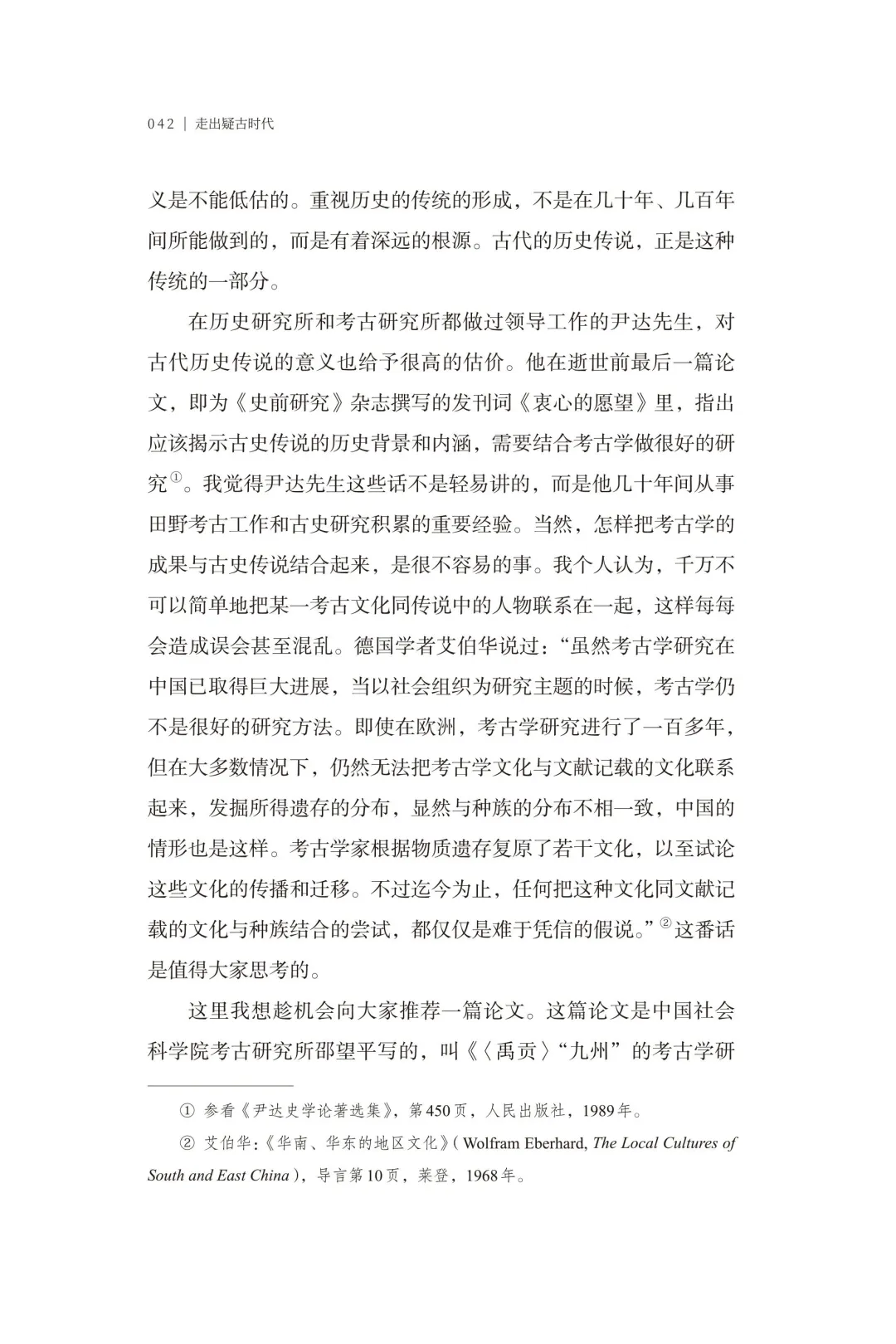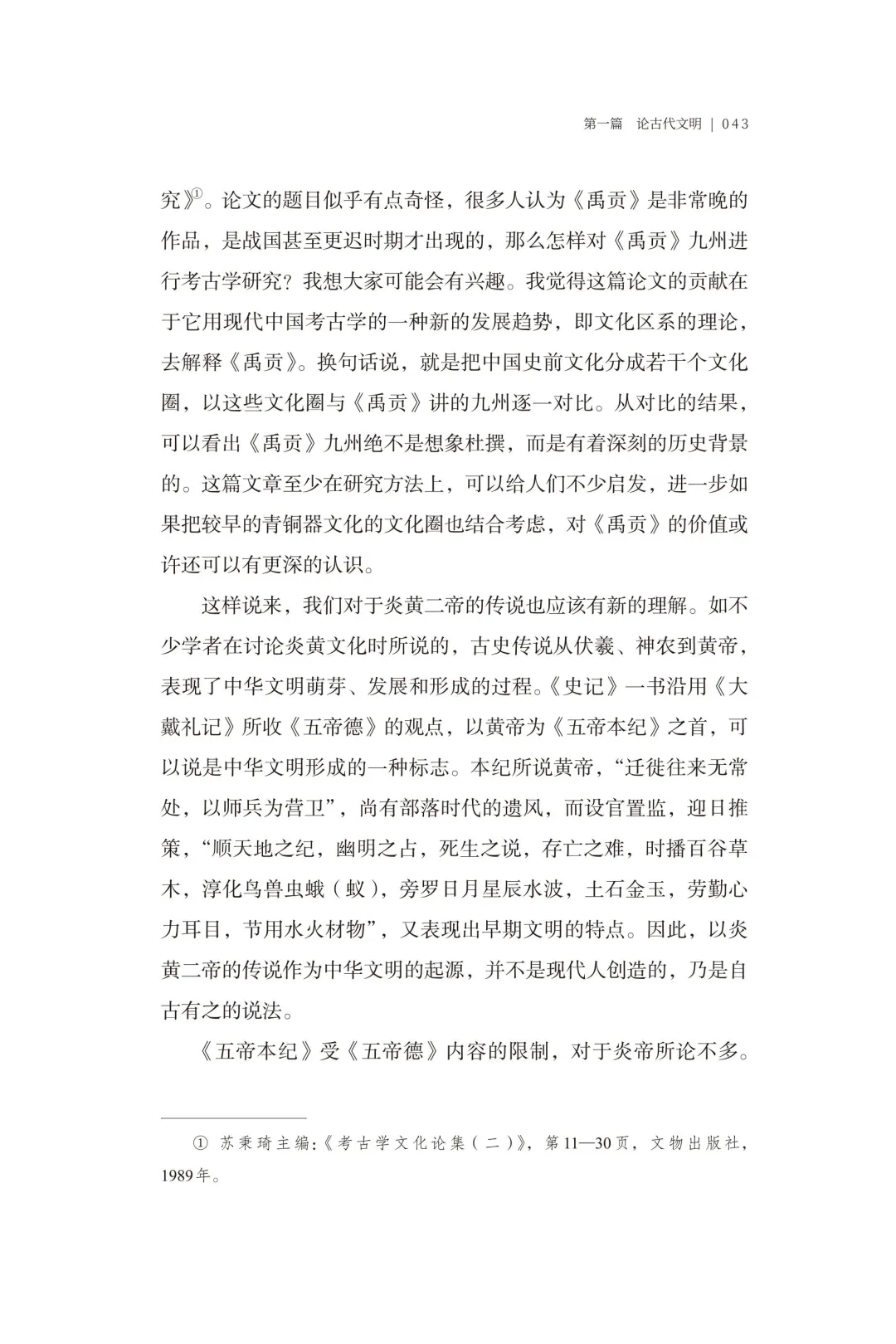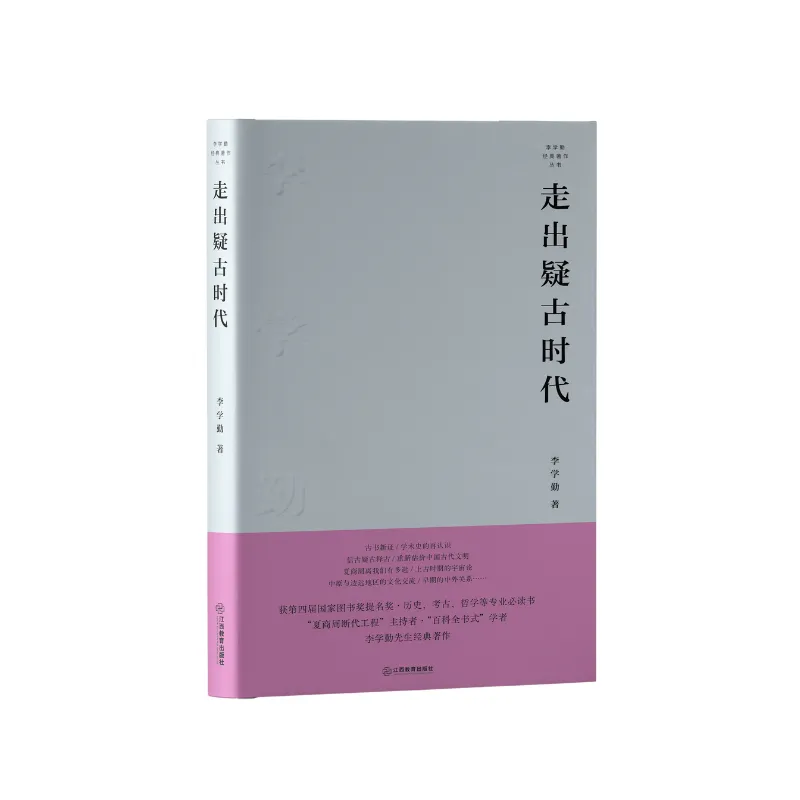
《走出疑古时代》
作者:李学勤
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月
定价:112.00元
ISBN:978-7-5705-4464-6
内容简介
《走出疑古时代》是一部考察、理解、比较和估价整个人类文明历史背景下中国古代文明特色和价值的经典著作,主要涉及中国上古时期的考古发现与历史文化、中原与边远地区的文化交流、早期的中外关系等内容。全书共分六篇,分别为论古代文明、神秘的古玉、新近考古发现、中原以外的古文化、海外文物拾珍、续见新知。本书初版即引发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走出疑古”的认识成为当代的一种学术思潮,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书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自序(节选)
在本书各篇节中,我着重谈几个问题,记在这里,以供读者参考:
一、上古时期的宇宙论(cosmology)。中国汉以前对宇宙的认识,有其明显的特征,富于哲学和科学史的意义。当时一些观念渊源久远,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时期。本书第二篇第四节《论含山凌家滩玉龟、玉版》、第三篇第一节《西水坡“龙虎墓”与四象的起源》等,均与之有关。前者曾以“A Neolithic Jade Plaque and Ancient Chinese Cosmology”为题,在1992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报告过。
二、饕餮纹的演变。所谓饕餮纹,在中国考古学、美术史、神话学等学科中,都有重要的位置,但其性质和源流迄今不很清楚。本书几处对此试做研讨,如第二篇第一节《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主旨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珀西沃·大卫基金会召开的“商代青铜器纹饰的意义”讨论会上提出。另外第三篇第二节、第四篇第七节等,也有涉及这一问题。
三、中原与边远地区文化的交流。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是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共同缔造的。我一直主张古代中原地区与边远地区的文化间存在着双向的传播影响。中原文化强烈地影响到很遥远的地区,同时在中原也能找到源于边远地区的许多文化因素。书中较多篇节谈到这个看法,而以第四篇更集中些。
四、早期的中外关系。本书第五篇论介了日本、韩国、阿富汗发现的若干文物,皆与当时中外的文化交往有关。比如日本、阿富汗出土的铜镜,可补充1991年出版的拙著《比较考古学随笔》的一些论述。日前我写了一篇小文,根据最新公布的材料,谈及商朝通向东南亚的道路,似可与“西南丝绸之路”相证,可惜其内容已不及纳入本书了。比较考古学方面的试探,我很想继续下去。
这里还应谈一下本书的标题。两年以前,我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整理后冠以此题,现在已用作本书导论。从这个标题委实容易联想到冯友兰先生30年代关于“信古、疑古、释古”的提法,我在导论中也确实引述了冯先生的话。
冯友兰先生这一见解见于《古史辨》第6册序,近来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信古、疑古、释古,指的是怎样看待文献记载的古代历史文化的问题。疑古是晚清今文经学一派率先倡导的一种思潮,反对古人对文献一味尊信,要求就古史普遍做理性的审查。疑古思潮在思想史上起过很大的进步作用,但因怀疑过度,难免造成古史的空白。这一思潮的影响深远,要对古代历史文化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不摆脱有关观点的约束。冯先生提出以释古代替疑古,确具卓识。如我在导论所说,有人建议把释古改为考古,考古是释古的关键方面,不过释古的含义比考古要更为广泛。
我常常揣想,冯友兰先生的提法应该和他任教多年的清华大学学风有关。大家知道,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导师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讲师为李济。那时,梁任公在清华执教有年,他以往曾认同“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但他这时的讲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议论已较持平。王国维先生对古文等问题做了许多切实研究,并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以地上、地下材料彼此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李济先生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更是中国人自行主持考古发掘之始。清华不少学者对古代的探究,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为释古之说开了先路。
信古、疑古、释古的提法,已经是学术史上的公案了。今天的中国考古学、历史学和文献学,都是相当发达成熟的学科。充分沟通这些学科的成果,将能进一步阐释古代的历史文化。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把中国古代文明放到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背景中,去考察、理解、比较和估价,从而做出具有理论高度的贡献。这是我长期企望的目标,却苦于力所未及。放在你们面前的这本小书,只能算是近期工作的一份报告,个中得失,敬请评判指教。
作者
1994年5月26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寓所
[摘自《走出疑古时代》,江西教育出版社2025年]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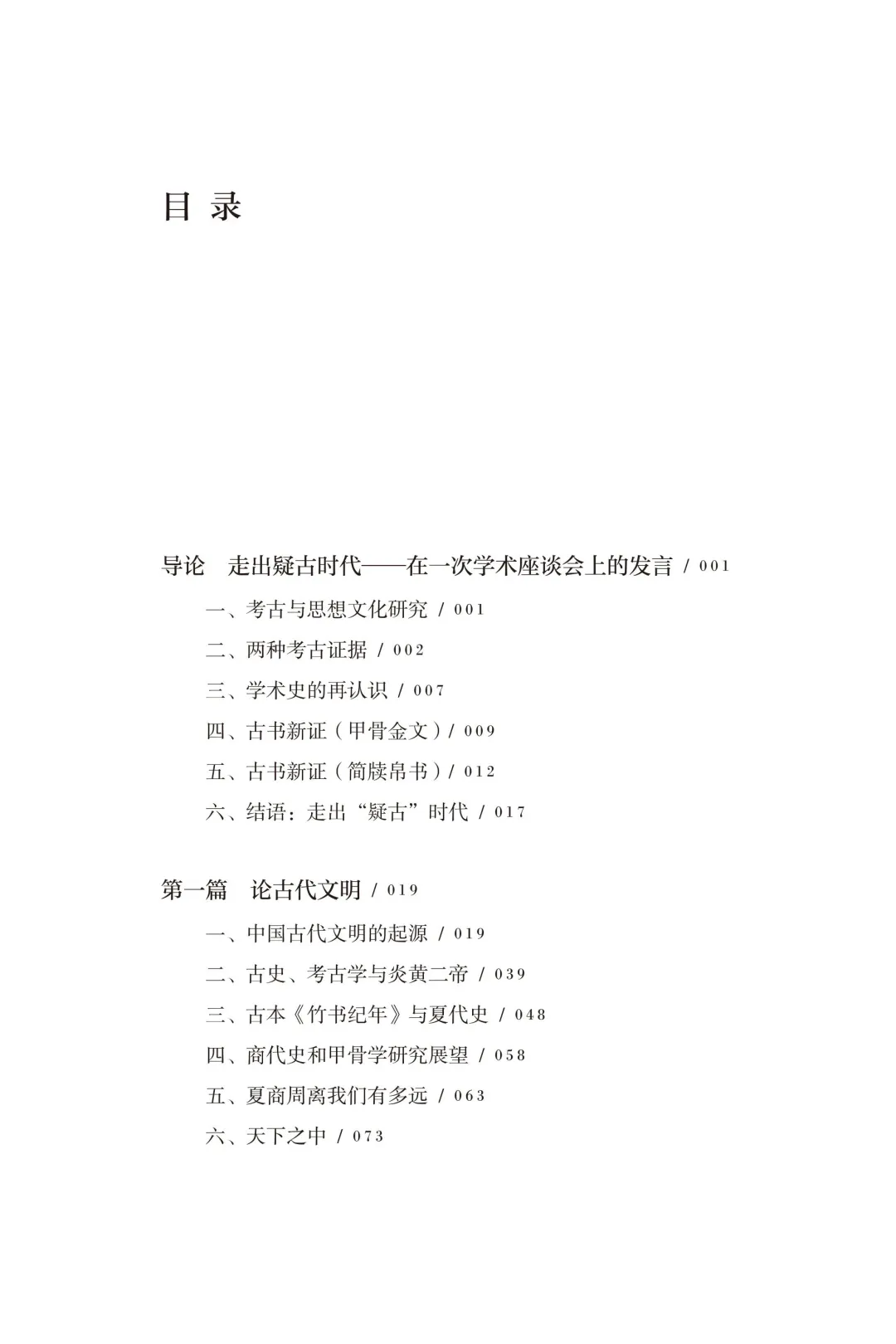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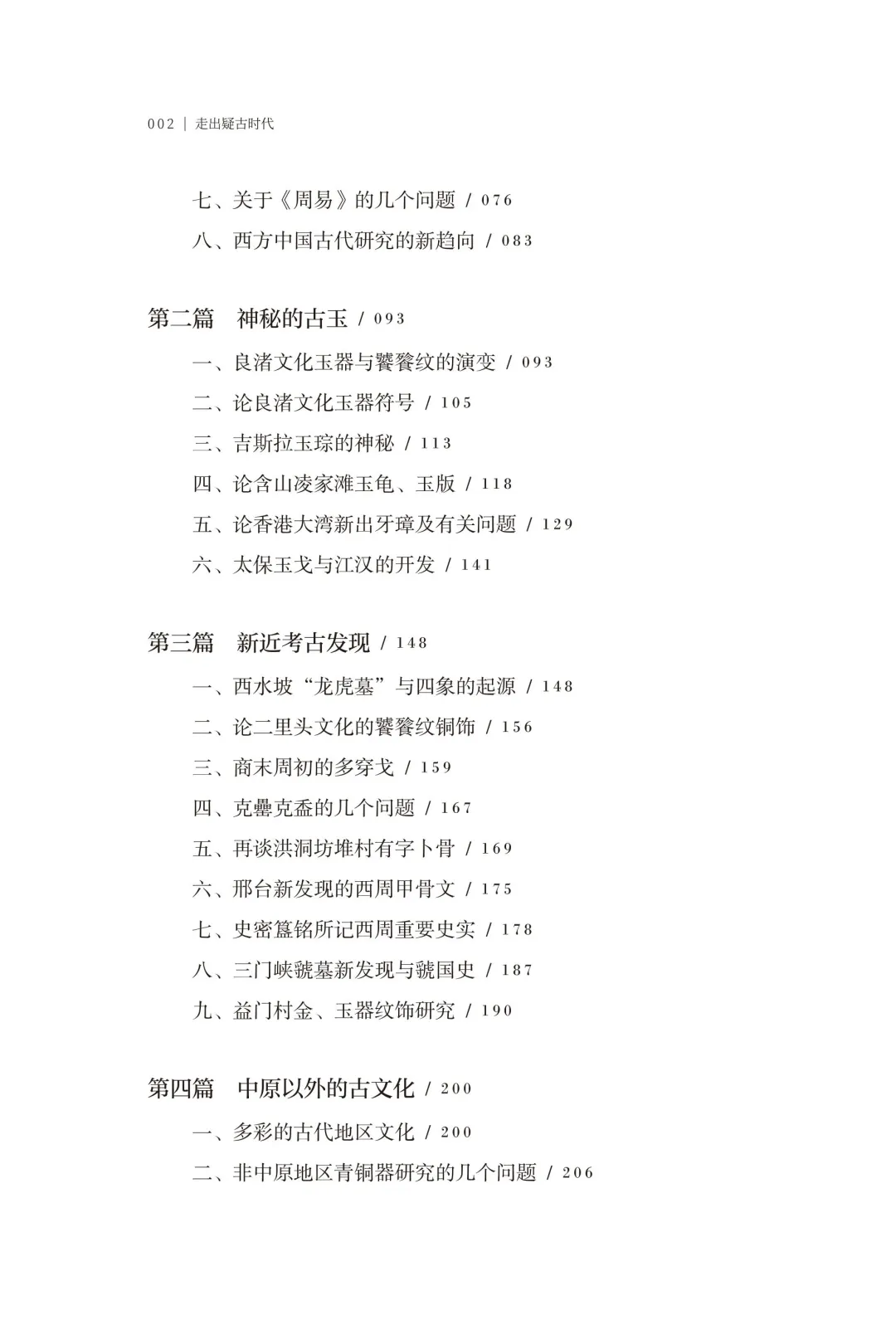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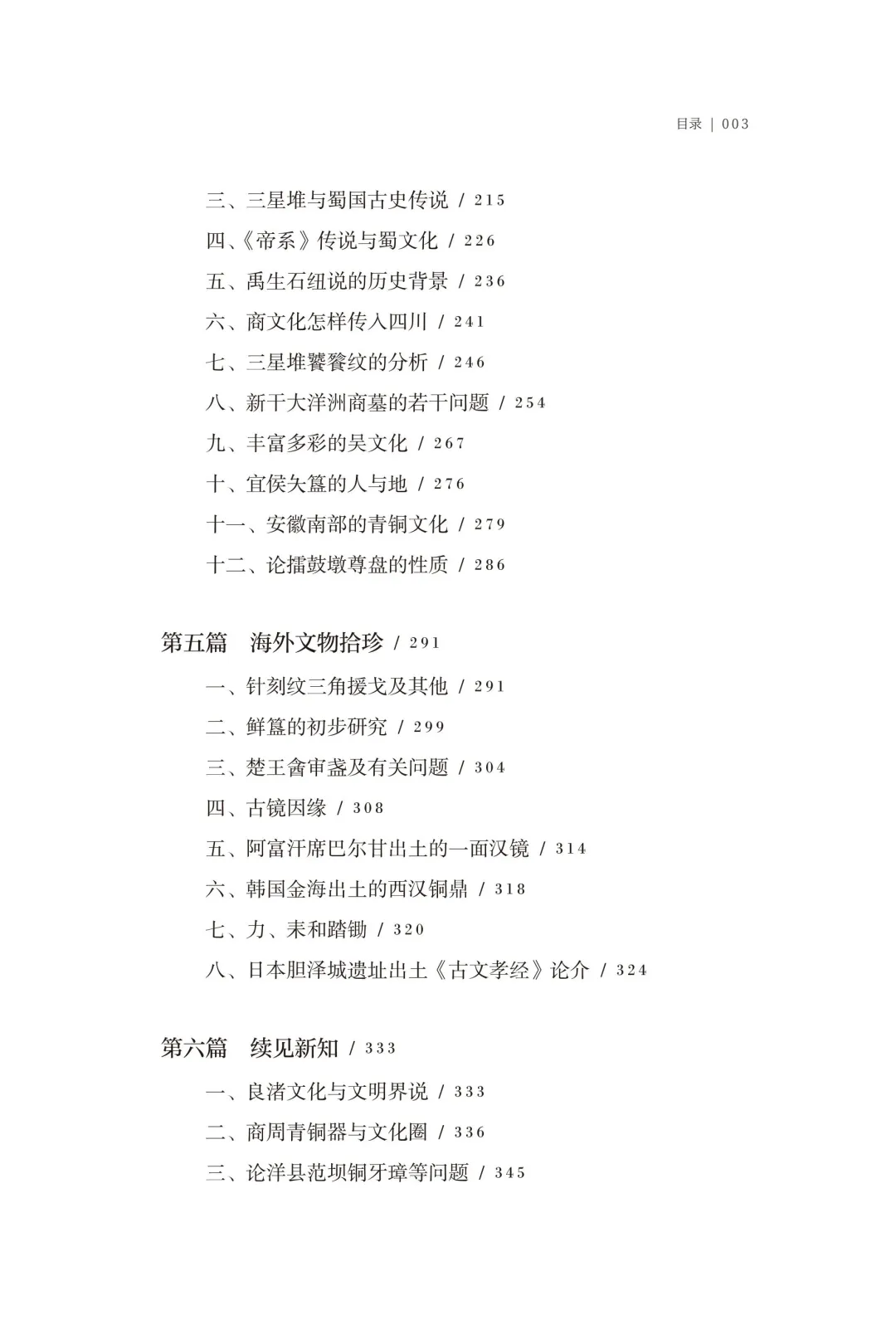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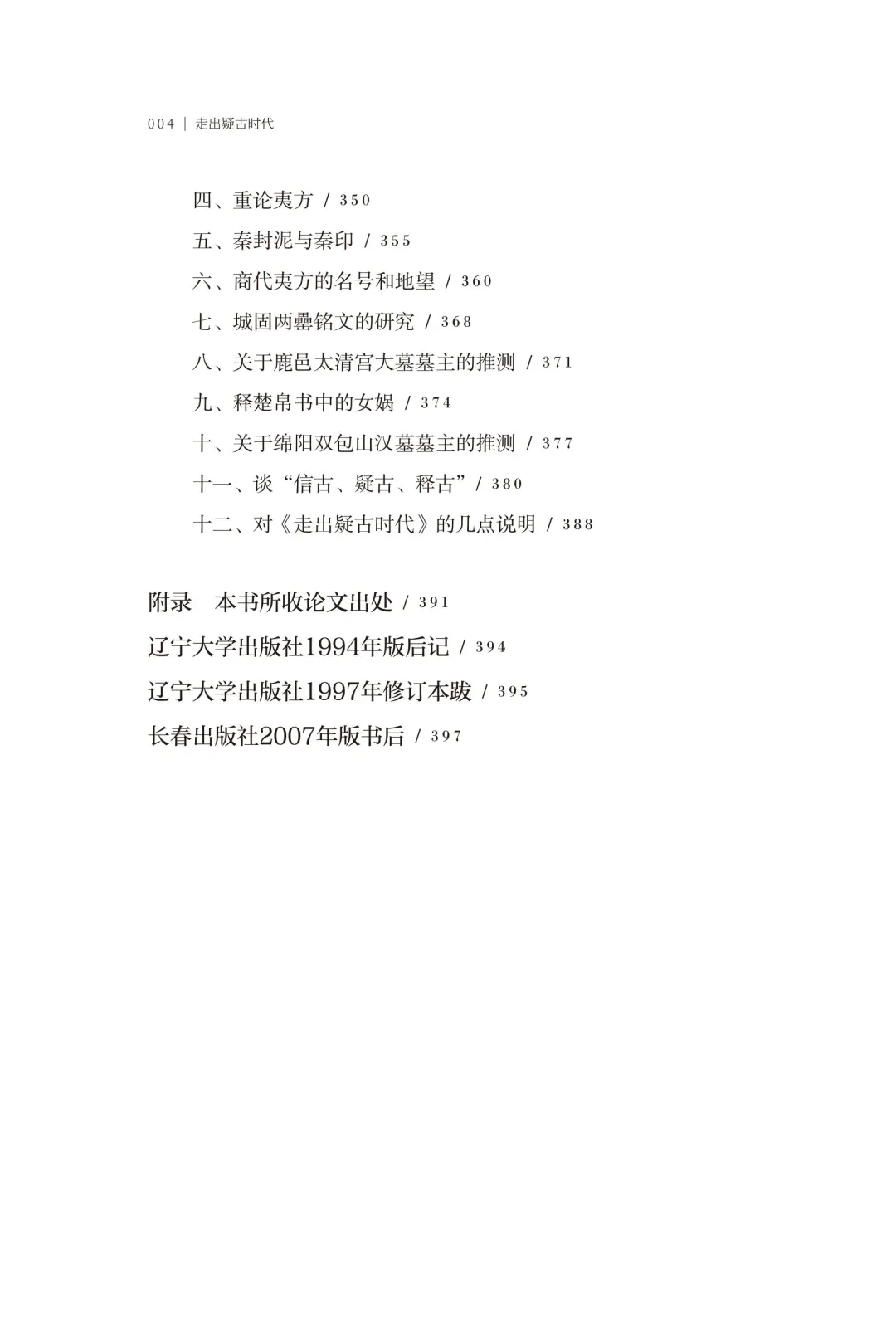
书影及试读书页